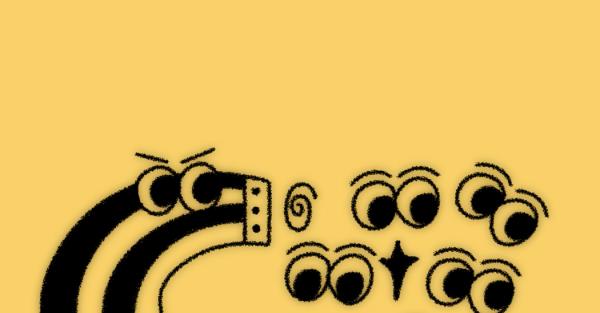
这种哀叹和教育本身一样古老:学生们没有认真听讲。但今天,注意力不集中或分散的问题已经达到了真正灾难性的程度。绝大多数高中和大学教师报告说,学生持续或深度注意力的能力急剧下降,严重阻碍了学习形式——阅读、欣赏艺术、圆桌讨论——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文科的核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你能有47秒的时间专注于一项独立的任务已经很幸运了。《米德尔马契》在这个时间轴上很难完成。有意义的生活、集体行动和政治参与产生的大多数形式的人类互动也是如此。
我们正在目睹新技术生活的阴暗面,其榨取的盈利模式相当于对人类进行系统的跟踪:将大量高压媒体内容注入我们的脸上,迫使我们产生一种被称为“注意力”的蒸汽和亲密的东西,这种东西现在在公开市场上交易。越来越强大的系统试图确保我们的注意力永远不会真正属于我们。
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剥削形式和人类苦难。然而,通过工会和劳工组织等新形式的活动,劳动人民推翻了“撒旦工厂”,这些工厂损害了他们的人性,从他们的血液和骨骼中榨取金钱。现在是时候进行一场新的、平行的革命,反对不诚实地剥夺你我的价值,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的价值。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抵抗力量,就像我们口袋里的小恶魔工厂一样。
这需要不断地关注,需要专门的空间来学习(或重新学习)这一宝贵的能力。在这些空间里,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物体、语言和其他人身上,从而塑造自己与共同世界的关系。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像学校,你是对的:这场革命从我们的教室开始。
我们必须改变教师们常年抱怨的局面。我们必须让注意力本身成为被教导的东西,而不是担心学生萎靡不振的注意力不利于教育。
这种转变的影响是巨大的。两个世纪以来,自由民主的拥护者们一致认为,个人和集体自由都需要识字。但是,随着人们对信息饱和和永远分散注意力的恐惧取代了对信息普及的呼吁,读写能力变得没有注意力(集中注意力的能力)那么紧迫。民主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专注的公民——能够一起从屏幕上抬起头来的人。
在世界各地,由教育者、活动家和艺术家组成的非正式联盟正在进行基层实验,试图让这成为可能——从作家珍妮·奥德尔(Jenny Odell)到哲学家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从调查科技伦理的大型项目人文技术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到慢读俱乐部(Slow Reading Club)的私密艺术活动。称之为关注行动主义。
我们三个都是这样一个团体的成员——斯特罗瑟激进关注学派。在教室里,在博物馆里,在公共图书馆里,在大学里,我们听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人们讲述他们如何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向世界和他人展示自己。他们描述的是注意力追踪所造成的损害,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称之为“认知不公正”的暴力。
我们开发的课程承担了我们许多人都面临的挑战:如何超越我们个性化的数字世界的限制,创造出类似于共享世界的东西。
它从个人和集体的体验开始,重点关注学生在阅读、观察、反思和解决问题方面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意识体验。考虑一个简单的练习,被称为“注意到位”,灵感来自实验作家乔治·佩雷克的作品。在他的短篇作品《在巴黎耗尽一个地方的尝试》(An Attempt at exhaustion a Place in Paris)中,佩雷克坐在他心爱的城市的一家街角咖啡馆里,用三天的时间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特别关注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可能不会被注意到的所谓平凡(他称之为“不平凡”)的事件。
在我们的短得多的练习中,在阅读了佩莱克的一段作品节选后,参与者前往社区,花30分钟的时间记下他们对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观察。回到小组后,我们围成一圈,从这些新发现的观察结果中,每人连续读一行。
听起来很简单!但结果非常接近奇迹:在集体关注的编织中重新发现了共同点。我所看见的,你都听见了;你感受到的微风也吹过我的角落。一首关于地方的共同之歌展开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集体感觉,即世界是我们的。第一人称复数成为现实,注意力的动态被揭示为我们个人在共享时间和空间中的舞蹈。
深刻的问题随之而来:语言和身份是如何构建我们能够看到和知道的东西的?当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感知世界时,我们如何改变世界——并努力阐明这些感知?我们从根本上共享(或不共享)这个世界的政治含义是什么?人们很快就明白,注意——给予和得到注意——构成了社会生活。
像这样的课题通常都是在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进行的。但我们在城市公园、esl教室、公共图书馆和课后心理健康项目中看到了这样的讨论,参与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发表权威言论,并承诺自己是一个敏感的注意力工具。
这种注意力教育的新范式要求我们深入挖掘这种工具的魔力。我们建立了每个使用它的人的联盟。这包括老师和学生,也包括焊工、冲浪者——任何用心做事、全身心投入的人,任何珍惜真正关注的人。
一小群人关掉手机,在当地的公园里集中注意力半个小时,这本身显然不是一场革命,不会让注意力追踪者屈服。但它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建立的模式,人们聚在一起决定(和争论!)世界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自由的实践——民主的本质——也是教育本身的崇高目的。
我们的注意力生来是自由的,但越来越多地处处受到束缚。我们的博雅教育体系能否应对这一挑战?哈佛大学(Harvard)政治哲学家丹妮尔·艾伦(Danielle Allen)最近写道:“我有一种预感,如果我们把这个注意力问题放在我们现在要求人文学科做的事情的中心,我们可能会发现人们对人文学科的工作有巨大的兴趣。”我们可能会改变我们在大学校园和其他环境中看到的动态,在这些环境中,人文学科的实践似乎正在溜走。”
所有关注过像古希腊语这样晦涩难懂的话题的人都知道,“危机”这个词源于一个意思是“决定”的词。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决定文科在21世纪到底要为什么服务。任何形式的教育都不能一下子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注意力教育可以培养出新一代的公民,他们有能力认真而谨慎地处理这些问题。
格雷厄姆·伯内特是普林斯顿大学亨利·查尔斯·利亚历史和科学史教授,也是《注意力的场景:心灵、时间和感官散文》的共同编辑。他是非营利机构持续关注研究所的创始人和主任。Alyssa Loh,电影制作人,圣丹斯学院和阿尔弗雷德·p·斯隆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曾联合执导短片《关于注意力的十二篇论文》。彼得·施密特(Peter Schmidt)是布鲁克林斯特罗瑟激进关注学院的项目主任。
《纽约时报》致力于发表给编辑的各种信件。我们想听听你对这篇文章或我们的任何文章的看法。这里有一些建议。这是我们的电子邮件:letters@nytimes.com。
在Facebook、Twitter (@NYTopinion)和Instagram上关注《纽约时报》的观点版块。
为您推荐:
- Billie Eilish说她“感觉我的身体多年来一直在煤气灯下” 2025-07-06
- 危险驾驶者因肇事逃逸致小学生及妹妹受伤被判入狱 2025-07-06
- 欧盟在6月28日前豁免萨哈林2号油田遵守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 2025-07-06
- 新疆喀什哪个县疫情(新疆喀什有新增病例吗) 2025-07-06
- 没有人会猜到这些非常酷的台灯来自沃尔玛 2025-07-06
- 英国劳斯莱斯前首席设计师在家门口遇害,享年74岁 2025-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