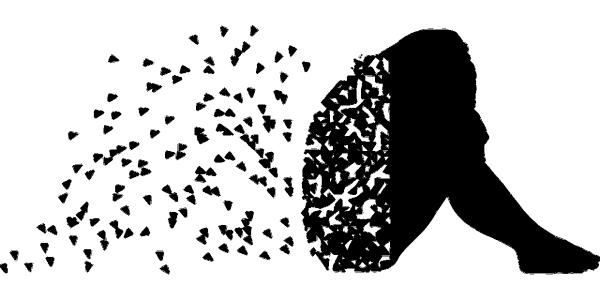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全球每年有超过70万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杀率在15-29岁年龄组尤其令人担忧,这是第四大死因。
有几个风险因素与自杀有关,包括家族史、人格特征、社会经济条件、接触社交媒体上的有害思想,以及精神障碍,尤其是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
“然而,尽管自杀死亡对心理、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但对自杀风险的识别是基于临床访谈的。
“与自杀行为相关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尚不清楚。
“他们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联合首席研究员、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UFSC)神经科学家Manuella Kaster博士说。
据她说,该小组审查并重新分析了科学文献中关于死后(死后)对自杀者的血液和脑组织进行检查时发现的分子变化的大量数据。
从17项研究中,研究的第一作者和UFSC博士候选人Caibe Alves Pereira通过合著者和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Unicamp)博士候选人Guilherme Reis-de-Oliveira开发的算法,对自杀和其他原因死亡的人的大脑基因和蛋白质表达变化的数据进行了回顾和分析。
抑制性神经递质的改变是在与自杀相关的生物学机制和途径中观察到的主要变化之一。
“分子改变首先与胶质细胞有关,如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它们与神经元密切而动态地相互作用,是控制细胞通讯、代谢和可塑性的基础,”该研究的联合首席研究员、Unicamp分子生物学家副教授Daniel Martins-de-Souza博士说。
分析还指出了某些转录因子(负责调节几种基因表达的分子)的改变。
“其中包括转录因子CREB1,它已经被广泛研究其对神经可塑性的影响,并作为抗抑郁药的重要靶点。
他说:“然而,转录因子MBNL1、U2AF和ZEB2与RNA(核糖核酸)剪接、皮质连接的形成和胶质细胞形成有关,但从未在抑郁症和自杀的背景下进行过研究。”
他补充说:“我们的结论是,在自杀行为等复杂情况下,这种分析作为识别易感性因素和潜在治疗目标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潜力。”
简单地说,分子改变可以被解释为“风险标记”,指出神经生物学的新途径,并为临床访谈中获得的信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在最初的研究中,前额皮质是最常被提及的大脑区域。
“这个大脑区域连接着所有的情绪和冲动控制中心。
“它在行为灵活性和决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其结构或功能的改变可能与自杀行为高度相关,”卡斯特教授说。
这对年轻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前额皮质是大脑中最后成熟的区域之一。
由于社会、文化、心理或其他因素导致的皮质可塑性的改变对15-29岁年龄组的情绪和行为控制有重大影响。
她说:“从几项研究中得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许多研究对象在自杀或企图自杀的前一年接受过健康服务,但由于难以识别风险,他们没有得到可以预防这种结果的护理。”
她补充说:“从构思到执行,自杀在各个方面都必须认真对待。
“我们知道自杀死亡在男性中更为普遍,而自杀未遂在女性中更为普遍,但这是由于所使用手段的潜在致命性和攻击性,以及行为差异。”
“如果干预及时,自杀是可以避免的死亡原因。
“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动机。
“应该与自杀的耻辱作斗争,以便对其各种生物学、社会和文化方面,特别是这些行为改变所涉及的机制,有一个深刻而广泛的理解。- jos
×
为您推荐:
- Nur Farah Kartini谋杀案的嫌疑人抵达法庭 2025-05-20
- 5月14日就法庭对海军学员祖尔法汉一案的裁决提出上诉的聆讯 2025-05-20
- 《罗马尼亚足球》谨慎乐观地认为,努力工作会有回报 2025-05-20
- 在自杀身亡的人身上发现大脑变化 2025-05-20
- 前历史老师Tokoh Guru Kebangsaan 2024 2025-05-20
- 令人难以置信的自驾游被评为“欧洲最佳之旅”,沿途尽是美丽的海滨城市 2025-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