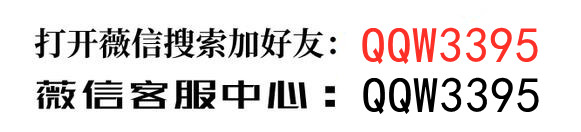电脑显示她是一位88岁的女性,主诉是疲劳。根据经验,我知道老年人的疲劳几乎可以由任何原因引起。那么,是心脏病发作吗?抑郁症?癌症吗?哪里感染了?还是她太累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在那里的真正原因。
那个瘦小的女人恰好坐在轮床的中央。她的白色网球鞋放在椅子下面,每双鞋里塞着一只厚实的肉色及膝长袜。椅子上放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黄色开襟羊毛衫,上面是一件同样叠得整整齐齐的棕色连衣裙。
她把病号服像夹克一样穿在身上,敞在胸前,她那疙疙瘩瘩的手紧紧地抓住病号服,盖在胸前的十字文胸和齐腰的白色棉质内裤上。她脖子上戴着一件天主教布料的肩胛,上面有一幅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用一根绳子挂在她脖子底部的凹处,一条细金链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金十字架。
“你好。我的名字是伯恩鲍默博士。看到美洲驼了吗?”我对她说。
“你好,Doctora。我叫玛丽亚,”她回答。
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她坐得更直了,她的姿势是一个发现生活有趣的人的姿势。我检查了她的臂章,并主动提出用折叠在脚边的床单盖住她。她点了点头。
我问她感觉如何。好吧,她告诉我。她有什么烦心事吗?不,她说。疼痛吗?不。有气短,胸痛,头痛吗?不,不,不。我看了我的单子,她否认有任何问题。
玛丽亚与医疗系统的唯一接触是在她的许多孩子出生时,其中有几个孩子比她活得更久。她在二十多年前就守寡了。她一个人住,家人住在附近。她没有工作,但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管家。没有药物,没有过敏,没有手术。
我问能不能给她检查一下,她点了点头。她从头到脚都非常健康。她那明亮而好奇的眼睛嵌在柔软的皮肤上,长时间的微笑形成了深深的鱼尾纹。她头部和颈部的其他检查都正常。脊椎有一点弯曲。肺部清晰,心跳强劲稳定,没有异常声音。腹部,四肢,神经检查,一切正常。
我很困惑。她期待地看着我。
“那么,你确定今天没什么烦心事吗?”我问。
她耸耸肩,举起双手,“你能怎么办?””的手势。
我一事无成。是时候换个策略了。
我问她为什么在急诊室。她说她不知道。
死胡同。
新的角度:“你今天是怎么来的?”
她的脸上绽放出笑容。她的女儿、孙女和曾孙都来过她家,把她抱起来送到急诊室。
最后。也许是答案。
在玛丽亚的允许下,我在候诊室找到了她的家人。他们很容易找到,三个人都很像那个轮床上的娇小女人。当我走近他们时,还是那双黑眼睛盯着我,她的眼睛明亮而好奇,而他们的眼睛却是红框的,眼睑肿胀。
当我们进入“家庭活动室”交谈时,两位女士听从了那个十几岁的男孩,他是发言人。他站着,我和女人们坐着。
他们都转向我,等待着。我清了清嗓子。
“那么,我在想,你今天为什么带玛丽亚来医院?”
三双眼睛顿时都噙满了泪水。最年长的女人向男孩点了点头,他说话了,目光垂向地板。
“我的表兄。他就死了。警察来到我姑姑家,告诉她他中枪了。”
“哦!我很抱歉。”现在我明白了泪水的含义。
我们又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没有人动。我还是不知道玛丽亚为什么会在那里。我大胆地问:“那么,你的曾祖母有什么问题吗?”
男孩回答说。“我的表兄。他是…曾经是…阿布丽塔的最爱。家里每个人都知道。”男孩的声音是恳求的,但我还是听不懂。“我们要你告诉她他死了,”他脱口而出。
它就在那里。

我希望我能否认,但我的第一反应是恼怒。真的吗?她没有医学上的问题吗?急诊室里挤满了人,有些人病得很重,而我只花了宝贵的15分钟在这上面?人们真的认为急诊室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然后他们三个人立刻开始交谈起来。他们担心她发现后会心脏病发作或中风。他们害怕这消息会害死她。他们不想告诉她。他们想让别人来做这件事,她需要一个地方,如果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她会得到照顾。
我听了他们的话坐了一会儿。我记得当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他大腿疼痛是由肺部肿块扩散而来的肿瘤引起的时候,我的感受。我记得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都会挺过来的,这个现在歪斜得可怕的世界,会以某种方式恢复正常。
最终发生的治愈并非来自与医生的任何讨论,而是来自于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给予彼此的爱和支持,来自于我们依偎在一起的时光,我们的手和头碰在一起,创造了一座大厦,一座我们都能从中汲取力量的尖塔。
通过这些回忆,我的前进道路变得清晰起来。
我吸了一口气,身体前倾,看着他们每个人的眼睛。当我告诉他们我会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我确保他们都听到了,包括玛丽亚。我说我会和他们在一起,在房间里,如果玛丽亚需要什么,我会在她身边几个小时看着她,确保她的安全,得到照顾。我告诉他们,我会支持他们,但这个消息必须由他们自己来传达。
他们互相打量着对方的脸,然后都点了点头。
我们都走进玛丽亚的房间,当她看到我们的脸时,灿烂的笑容消失了。他们走到她的床边。我把一盒纸巾放到玛丽亚旁边的桌子上,然后走开了。
玛丽亚现在被她的三代子孙包围着。他们低声用西班牙语和她交谈,我看着四个人——四代人——面对这个可怕的消息。
玛丽亚静静地听着。她笔直的姿势稍有松动,她的笑容消失了,她的脸瞬间老了几十岁。她向家人伸出一只手,这只手由于多年的劳动而变得老态龙钟和畸形,他们都牵起了手。她用另一只手抓住自己的肩胛骨,轻轻地拉着脖子上的绳子。
我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靠在走廊的墙上回忆起来。
我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全身心地关心他人,并决定自己的未来是在医学上。为了成为一名医生,我愉快地接受了多年的教育、培训和债务。我回忆起学习人体的兴奋感,它是如何工作的,当它不起作用时该怎么做。
我记得当我学会开始静脉注射时,病人痛苦地喘着气,我畏缩了。当我第一次告诉病人他们得了绝症时,我的心都碎了。作为一名三年级的医学生,有一天晚上我哭着睡着了,我确信在他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中会好起来的那个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但我不记得我的同理心是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
我知道,当我开始轮班时,我走过一个挤满了护理人员、轮床和病人的救护车区。我知道,无论我多努力,多快,候诊室永远不会空无一人。当病人受伤或生病时,他们也会来急诊室,但当他们不能去看自己的医生时,或者当他们失去了保险时,或者因为下班后是他们在工作之间唯一的休息时间。警察带来了无处可去的病人,或者有行为问题的病人,或者是那些瘾已经吞噬了他们生活的病人。
病床总是不够用,病人等了好几个小时,每个人——病人和工作人员——都很累,很生气,这是可以理解的。没有办法把工作做好——至少没有我被训练得那么好。尽管如此,行政上的精打细算者还是把我的工作效率降低到计算每小时看了多少病人,安排了多少检查。
当我成为一名急诊医生时,我一直在承担繁重的工作、不稳定的时间表、艰难的决定和繁忙的轮班,这些都伴随着这份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让一个不断变化的、压力过大的、破碎的系统的要求把我赶出了轨道。
站在走廊里,听着玛丽亚和她的家人轻声细语,我想起了我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我选择这个职业,为什么我疯狂地工作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我做这份工作。
我从墙上挣脱出来,去照顾下一个等着看的病人。
玛丽亚没有心脏病发作,也没有中风。一个小时后,她让她的曾孙来找我,告诉我她想离开。她的家人帮她穿上衣服,收拾好她的东西,而我则准备送她回家所需的东西。在她的房间门口,我依次拥抱了他们每个人,最后一个拥抱了玛丽亚,因为我知道她去急诊室正是她和她的家人所需要的。
显然,这也是我所需要的。
注:为保护上述个人的隐私,一些姓名和识别细节已被更改Ned在这篇文章中。
黛安·伯恩鲍默是一位住在洛杉矶的急诊医生和作家。她的诗歌和散文发表在《Intima:叙事医学杂志》、《急诊医学年鉴》和《内科医学年鉴》等医学期刊上,以及《他们写的东西:一个写作/治疗项目》选集,由《Room:分析行动的速写本》出版。她是专栏项目的大使,并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扩展分校的作家项目。
已经贡献了吗?登录以隐藏这些消息。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什么故事?在这里找到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并发送给我们pitch@huffpost.com。
为您推荐:
- 3分钟学会“手机拼三张可以开挂吗”(原来确实是有挂) 2025-05-02
- 我来教你“乐胡麻将开挂神器”其实有挂 2025-05-02
- 据报道,俄罗斯军队前进时抓获了一名为乌克兰作战的英国人 2025-05-02
- 埃文代尔高地男子承认忽视狗 2025-05-02
- 给大家通报一下“全民内蒙古麻将可以挂吗”确实是有挂 2025-05-02
- 教你使用“逍遥卡五星有挂吗”真实有挂 2025-05-02